讓「曖昧」動員觀眾的注意與想像
身為法國劇壇少數集編導於一身的劇場人,波默拉被稱為「舞台的作者」,他除了關注當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如何異化扭曲人類生活等社會議題,亦從經典童話取材,賦予全新意涵。他說:「不管是劇本創作或導演,我認為都不應該全盤托出或毫無保留地呈現,反而要提出可能性,為觀眾的想像力打下基礎,讓他自己能夠創造。」
訪問、翻譯 王世偉
訪談記錄 Marion Boudier
在法國中生代劇場導演中,喬埃・波默拉是少數身兼劇作家與導演雙重身分的創作奇才。他所有作品都是自編自導,他認為,只有劇作家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劇作,也最可以掌握導演方向。評論者稱波默拉為「舞台的作者」,因為他擅於將各種劇場元素,融合在文字之中,創造出獨特的舞台美學。
波默拉除了關注當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如何異化扭曲人類生活等社會議題,亦從經典童話取材,賦予全新意涵。他的作品屢獲法國戲劇大獎,包括劇場評論學會大獎(Grand Prix du Théâtre du Syndicat de la Critique)、戲劇文學大獎(Grand Prix de Littérature Dramatique)及莫里哀獎(Molière Award)等。波默拉不僅自創劇團,2007 年,在彼得.布魯克的邀請下,他擔任巴黎北方劇院(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的駐團藝術家,亦曾任巴黎歐德翁歐洲劇院(Odéon Theatre de I’Europe)聯合藝術家,現於布魯塞爾比利時國家劇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Bruxelles)出任相同職位。趁 《仙杜拉》 Cendrillon即將在台灣上演之際,本刊透過 email 專訪,邀請他分享創作歷程與劇場編導的種種思索。
Q:您改編民間故事的 3 部曲,都觸及兒童面臨成人世界後所發生的變化。為何您想要處理這樣的主題?在這三齣改編童話的作品中,您使用哪些不一樣的方法,讓年輕觀眾能意識到這一段人生的轉變?
A:我迄今重寫了 3 部童話,或是 3 個民間故事:《小紅帽》、《皮諾丘》 和 《仙杜拉》。在這 3 部作品中,主要的人物都是小孩,在他們成長的路途上都出現一種啟示:某些東西一開始被忽略了,但最後被發現。讓我想要改編童話的原因,其實是一種寫作的衝動。開始重寫 《小紅帽》 時,我想讓自己最小的女兒認識我的工作,也是因為它是讓我——不論是個孩子還是成人——都感到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不認為童話的讀者只限於孩子。《小紅帽》、《皮諾丘》 和 《仙杜拉》 的故事對所有人類來說都是最根本的經驗:譬如說,害怕的、慾望的、死亡的、孤獨的、自由的經驗。它們都是共存最基礎的經驗。例如,當皮諾丘來到世上,懷抱著一種慾望,它就是一切的中心。就像是世界是為了它而生一樣,沒有像它一樣的同類存在著。皮諾丘必須體驗與其他角色的關係:這就是生命的學習。
當我重寫一部童話,我試著讓它在當代引發回響。也就是說,我試著以真實的角度重新描述虛構的故事,盡可能用最簡單、最確實的筆調。舉例來說,《仙杜拉》 中,我企圖擺脫佩侯(Charles Perrault)(註1)時期的社會道德和傳統想像中的迷人王子。我重新改寫這個故事是因為關於死亡的疑問。在我的戲裡,珊德拉(仙杜拉)自己決定每個小時要思念已逝的母親一次,她認為這是一種義務 :我以這個年輕女孩對自己施展的暴力為探索的依據,去質疑仙杜拉給人良善的刻板印象。
除了用適合孩子的語言敘事,我在演出形式上(指導演員表演的方法,燈光、聲音、空間的關係)並沒有改變熟悉的手法。舉例來說,我尋找清楚可辨識的線條與引發想像地帶之間的平衡。童話只描繪事物而非闡明:我喜歡這種敘事的節約和它開展的想像空間。例如,在《小紅帽》中我們特別用心處理昏暗的部分,為了突顯野狼挑起、交織著慾望和害怕的感受,也讓觀眾用自己的想像力建構全部的場景。在我重新改寫的三部童話中,身兼重要角色的敘事者也同樣會激發觀眾的觀感。
Q:您的劇作通常從類似情節劇的狀況出發,藉以提出生存性的問題。您認為透過這種形式,劇場比較容易與一般觀眾溝通嗎?您如何從個人故事引伸出社會問題?隨著演出構成,您是如何發展您的提問?
A:或許要先弄清楚您所謂的「情節劇」是什麼意思,因為對我來說,這指的是經過許多波折累積而成、被誇大的狀況,這絕不是我會用來形容自己劇作的字眼。在我的某些劇本中,的確出現一些有點出乎意料的翻轉,例如像在 《我的冷房》 中,布洛克最後把自己的公司讓給所有員工,或是 《圓圈/虛構》 中的階級晉升幾乎都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我覺得尋常的人物面對離奇狀況是非常有趣的,這可以讓我們觀察到其中的過程、人性的反應和情感。有時候,這也產生了一種幽默的形式,我覺得要談到社會暴力的現實,這種形式是必要的。
有點像是人類學家,我並不會分離人類與他們的環境,所以社會和私人問題必定會融合在一起。唯有深入情境的實際狀況,個人生活經驗的具體性,我覺得才能觸及社會問題。寫作上,選擇如家庭或是公司的群體,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其中的關係很單純、比較好懂,不需要用太多的解釋來滿足觀眾的想像。
每一齣戲的劇本寫作的發展都不一樣。我一邊寫作、一邊導戲。並沒有什麼一蹴可幾的方法。我與藝術團隊、演員們密切合作,慢慢具體化我的想像,特別是有方向性的即興發展階段。但每一齣戲,創作過程都會改變。有時候我在排練初期已經想好一個主題或是一個畫面,有時候我已經有一些文本片段或一個故事的想法,有時候只憑一種直覺……
(欲看全文請購買 《PAR表演藝術》 雜誌 2015 年 11 月號 275 期,免費下載 《PAR表演藝術》 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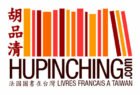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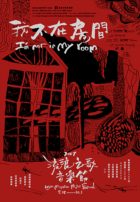

















Commentaires